取自【蕭十一郎】第11集
作者:秋風劍
2002/07/31
連家堡的夜裡,蕭十一郎忽覺門外有人,迅速地將門打開,眼光環顧四周,已然縱身躍出。他向前邁開幾步,站在月光下,毫不畏懼,沉著地道:「朋友,既然來了還不現身!」只見一個朦朧人影伴著示意「小聲點!」的噓聲從黑暗中漸漸明朗,卻是城瑾。
蕭十一郎愣了一下,本來嚴陣以待的武裝頓時鬆懈,面對城瑾,他又故意裝作一副吊兒啷噹的模樣,道:「沆∼是妳啊?半夜三更不睡覺,跑到這兒來餵蚊子啊?」城瑾怕他發出太大的聲音,仍連連示意他安靜,以半命令的口吻道:「小聲點兒!我不想讓人家看見是我來找你的。」城瑾心中雖然對蕭十一郎有好感,卻還不願意教大家知道自己喜歡他,但如果大家知道的是蕭十一郎喜歡自己,那就無所謂。
蕭十一郎卻因白天一場誤會,又身處連城璧的地盤,為了要能守護好割鹿刀,實在不想再多生是非,對城瑾道:「妳那麼想就對了嘛,回去吧!」說罷轉身便要回房,城瑾也被他唬了一下,當真要回房去,走了兩三步才發現不對,趕緊回頭將他攔住,道:「喂!你忘了我中毒了嗎?」蕭十一郎道:「妳忘了有白楊綠柳啦?」城瑾向來嬌生慣養,半撒嬌半耍著無賴地道:「就是找不到他們嘛!」定要「喜歡她」的蕭十一郎陪她去找。
蕭十郎道:「那妳就快去找啊!」他仍擺出一副不耐煩的樣子,但心思仍像個孩子般的城瑾並未發覺,仍堅持地道:「不要!我現在要你陪我一起去找,走!」拉起蕭十一郎的手便要走。蕭十一郎將手拉回來,想盡最後的努力擺脫這場麻煩,認真地道:「哎呀!妳不是不想讓人家看到我們在一起嗎?」不料城瑾卻道:「別人呢看到你跟我在一起是沒有關係的,只要別讓人家看到是我來找你的就行了。」
蕭十一郎一臉困愕,不解地道:「有差別嗎?」城瑾道:「差遠了!我是連家大小姐啊。」面對如此任性驕縱的城瑾,蕭十一郎也不生氣,只是嘆了一口氣道:「我看得出來呀,是你們連家的血緣,兄妹倆完全一個樣。」城瑾也不管蕭十一郎的反應,硬是拉著蕭十一郎道:「好啦,走!」蕭十一郎無奈,邊裝作睡眼矇矓唉聲嘆氣,邊被毫不在乎的城瑾拉著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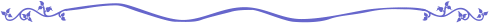
連家堡的另一個角落,連城璧正和綠柳商討對付逍遙侯的大計。連城璧問道:「都交代清楚、佈置妥當了嗎?」綠柳道:「放心吧,少主!全都準備好了。」他總是盡其所能地完成連城璧託付的使命。連城璧現出自信得意的笑容道:「唯一的愛徒,一晚上沒回去,也許逍遙侯明天早上就會來找人了。」說到這裡,面上的表情又逐漸轉為可怕的冷肅,續道:「小心的守著吧!」綠柳對道:「是!」說罷領命而去。
連城璧露出自負的神色,自言自語道:「蕭十一郎,等我抓到逍遙侯,你才知道我連城璧的本事。保護割鹿刀,保護我,哼!不必了!」雖然已經知道,蕭十一郎到連家堡來的目的不是為了接近璧君,是為了保護割鹿刀,但他依然不敢確信璧君不會和蕭十一郎發生不應有的情感,況且以他堂堂連少堡主的身分,又怎能忍得下竟要靠一介大盜來保護自己。求勝的慾望之火在他心中熊熊地燃燒著,他要贏過蕭十一郎,他一定要勝過蕭十一郎,他要證明給璧君和所有的人看,他的能力是遠勝過蕭十一郎的,蕭十一郎拿不住逍遙侯,而他做得到,即使連白楊、綠柳都認為蕭十一郎的武功比他高出許多,但沒關係,高手過招,比的可不只是武功,還有智慧,他要蕭十一郎在璧君面前敗給自己,輸得慘慘的,讓蕭十一郎永遠沒有能力和機會可以將璧君從他身邊奪走,如此一來,他就是勝利者,贏得璧君的勝利者。
連城璧走向璧君的房間,想去看看璧君。他不僅要證明自己的能力比蕭十一郎強,更要璧君對自己有好感,如此一來,璧君才會永遠是自己的,再也跑不掉。走到半路,見到園裡的許多紅玫瑰,便順手摘了一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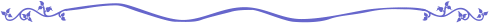
璧君在房內,正欲就寢,渾然不知逍遙侯正從門縫間悄悄潛入。當她慢慢地放下床帘,忽地一陣狂風將床帘漫天捲起,接踵而來的低沉奸笑,讓璧君驚駭地尖叫了起來。她四處張望,卻不見任何人影,又聽那低沉的嗓音開始說話:「告訴我,他們抓的人關在哪裡?」這使得璧君更加害怕,當她緩緩回頭之際,忽地,一個高大的黑影出現在眼前,卻是逍遙侯,璧君又再度被嚇得尖叫出來。
逍遙侯一手扼住璧君,威脅道:「他們在哪裡?我四處找,都找不到他們!」璧君什麼都不知道,又被扼得痛苦,幾乎無法呼吸,只能不住地搖頭。逍遙侯急著逼出答案,仍緊緊地掐住璧君道:「在哪兒?快說!我告訴妳,我並不想傷害妳,但如果妳不說的話,我就弄死妳。說!在哪裡?」璧君幾乎要哭了出來,卻只能不住地搖著頭,畢竟,這件事她確實全然不知。
此時,連城璧拿著剛摘下的玫瑰,來敲璧君的房門。他喚著:「璧君!」璧君想要呼救,卻被逍遙侯威脅道:「快打發他走!我就在妳背後,如果妳敢給他一點暗示,我就殺了妳!」才剛說完,連城璧又已在門外催著:「璧君!」見裡頭都沒有反應,又道:「園子裡的花開了,我給妳摘了一朵!璧君,可以開門讓我進來嗎?我…我想跟妳說幾句話。」房內,逍遙侯勒著璧君,又威脅道:「快點說!說!」璧君只好道:「我想睡了。」連城璧又道:「妳別這樣對我,我們可以從頭開始呀,我們可以…」他想為白天要利用璧君拔開割鹿刀的事找理由推託,請求璧君的原諒,重得她的心。
璧君面對威脅,根本無暇多想,只能道:「不,明天吧!」連城璧黯然地看了看手裡的玫瑰,想不到璧君竟不給他機會,將玫瑰捏了,轉身便要走。忽然,「乓」的一陣聲響從璧君房內傳出,那是璧君掙扎時,不小心將桌上的杯子摔碎所發出的聲音,逍遙侯續威脅道:「還不說!」連城璧聽見聲響,心頭一驚,直衝進璧君房裡,大喊道:「蕭十一郎!」
逍遙侯見連城璧來,慌忙逃走,連城璧看到逍遙侯逃去的身影,以為是蕭十一郎,又大叫著:「蕭十一郎!」想要追上去,被璧君攔住道:「不要啊!危險吶!」此時,蕭十一郎陪著城瑾找白楊、綠柳,正來到璧君房間附近,聽到連城璧急聲呼喚,城瑾對蕭十一郎道:「大哥叫你呢!」蕭十一郎以為連城璧出事了,正需要幫助,二話不說便向璧君房裡趕去。
連城璧被璧君攔住,仍一邊大喊著「蕭十一郎!」一邊想要追將出去,璧君緊張地道:「別去呀!危險啊!」卻被他一把推開,並用力朝璧君摑了一巴掌道:「不知廉恥!」正好蕭十一郎和城瑾趕到,璧君被打倒在椅子上,萬念俱灰,想不到自己竟嫁了這樣一個夫君,對他,她的心不能不死。見到這一幕,城瑾驚得滿臉錯愕,蕭十一郎心痛震驚,他想不通連城璧為何竟會如此對待璧君,剎時間,四人都沒有說話,現場一片沉寂。
連城璧之所以一聽見璧君的房內有聲響,就立刻判定是蕭十一郎,是因為他根本一點都不信任璧君,並將她想得非常不堪,懷疑她與蕭十一郎有染。他心裡一直存在一個問號,懷疑璧君的貞節,一心一意只想快一點證明自己勝過蕭十一郎,而非真愛著璧君。以至於當璧君發生危險,發出求救訊號時,他想到的卻是璧君與蕭十一郎通姦;當璧君擔心他的安危,阻止他前去追趕逍遙侯時,他想到的卻是璧君在掩護蕭十一郎逃跑。他根本不愛璧君,他愛的是自己的成功,他輸不起,尤其是輸給蕭十一郎。他總把打敗蕭十一郎視為第一要務,而不是璧君的安危,所以,當璧君發生危險時,他的第一念頭,不是要保護璧君,而是找蕭十一郎算帳。他埋藏在心底的虛榮心、好勝心、忌妒心、以及對璧君的懷疑、不信任,全在此時不可遏止地爆發了出來。
停了一會兒,連城璧又道:「原來如此,我說妳怎麼都不肯開門呀!我說妳怎麼總是看我,都不對呢?」他不檢討自己是用什麼態度對待璧君的,反而責怪璧君的不是。
連城璧粗暴地一把拉起癱倒在椅子上的璧君,責問道:「妳到底為什麼嫁給我?為什麼嫁給我?說實話!說實話呀!」連城璧用一雙鐵腕緊緊扣住璧君,不斷地搖晃她、逼問她,璧君吃痛,叫了出來,蕭十一郎看著,此時再也忍不住,一心只想著要保護璧君,再也顧不得其他許多,衝上前去,對連城璧吼道:「放開她!」同時一把將連城璧推開。連城璧還想上前責問璧君,被城瑾擋住,城瑾道:「唉呀!哥!你幹嘛呀?哥!」
璧君在一旁,已面無表情、欲哭無淚,心下冷然,一手護著差一點被逍遙侯勒斃的頸子,蕭十一郎在一旁看著她,心疼不已,目光中流露著萬分不捨的無奈。連城璧卻對蕭十一郎道:「你還有臉回來?你走!別再讓我看見你!」他仍以為蕭十一郎與璧君作了茍且之事,慌忙逃跑後卻又回來。在他被忌妒心蒙蔽的盛怒之際,又怎會想到,以蕭十一郎武功之高,就算他真是躲在璧君房中,又怎會不小心打破杯子?又怎會想到,蕭十一郎既慌張逃出,又怎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和城瑾一起出現?
城瑾心思單純,並沒有想到連城璧誤會沈璧君的後面,是這許多深沉複雜的原因,聽見連城璧這樣對蕭十一郎講話,先是覺得疑惑,接著便是生氣,見連城璧要趕蕭十一郎走,便大聲叫道:「不許走!你幹什麼呀,哥?就算給人家判了私刑你也得有個罪名呀!他今天救了我,又陪著我忙了大半夜,沒頭沒腦的你為什麼要趕人家走啊?」連城璧心中一懍,問城瑾道:「他剛才一直和你在一起?」城瑾道:「是啊!」連城璧這才發現自己似乎想錯了,問道:「那來的是誰啊?」
蕭十一郎用充滿不屑的眼神斜睨了連城璧一眼,如今連城璧即使欺侮羞辱的是自己,蕭十一郎都不會用這種眼光看他,可是他居然如此對待他純善的妻子──璧君,他竟會把純潔的璧君想得如此不堪,正反映著他自己內心的齷齪,這才使得蕭十一郎對連城璧的為人感到相當的不齒。璧君依然面無表情,只簡單地回答了三個字:「逍遙侯。」連城璧或者是心急於儘快抓到逍遙侯,以證明自己的勝利,或者是為了掩飾自己誤解璧君的尷尬,因為在城瑾證明蕭十一郎的清白之後,他方才一切侮辱璧君的行為與言論,都是在侮辱著自己,所以他只匆匆地道了一句:「已經來了!」便衝出了房間,追逍遙侯去了,城瑾喊著:「哥!危險啊!」也跟著衝了出去,房內,只剩下蕭十一郎和璧君兩人。
蕭十一郎守著璧君,過了一會兒,才道:「妳沒事吧?」見到璧君如此模樣,蕭十一郎的心在淌血。他無法替璧君承受連城璧對她的傷害,而且他深知,如此深的傷害是無法用任何言語來安慰的,他唯一能做的,只是用自己的心,緊緊地陪著她、守著她、護著她。璧君內心的痛苦,蕭十一郎全都瞭解,如果可以,他願為她承受一切。
璧君緩緩地搖了搖頭,頓了一會兒,道:「我沒事。」目光透著心冷心死的絕望無神,卻仍對蕭十一郎道:「去幫他。」蕭十一郎也無目標地凝望遠方,道:「他不需要我幫,他應付得來的。」語氣中帶著幾分怒意。
璧君雙臂交叉環抱著自己,手不斷來回搓動摩擦著,蕭十一郎見狀,道:「妳真的沒事?」璧君道:「好冷!」蕭十一郎二話不說,便除下自己身上的外衫,要替璧君披上,璧君搖了搖頭,推了蕭十一郎的衣,道:「是心冷。」蕭十一郎聽她如此說,心中萬分不捨,道:「我知道!」他完全能夠瞭解璧君現在內心痛苦絕望的滋味,他深深地瞭解。
蕭十一郎知道,璧君全心地把自己託付給連城璧,可是連城璧非但沒有以誠相待,非但不能保護自己的生命不受威脅,還將自己的善意想得如此不堪,面對如此的丈夫,璧君覺得,自己什麼也沒有了,所以他對璧君道:「可妳還有我啊。」他只想讓璧君知道,無論發生什麼事,無論連城璧如何待她,他都一定會陪著她、守著她。聽到如此簡單卻可靠堅定的回答,璧君終於忍不住了,淚水奪眶而出,她抱住蕭十一郎,趴在他結實的胸膛上哭了起來。蕭十一郎站得穩穩的,任她抱著、靠著,心疼難捨,恨不得能緊緊地抱住她,給她所有的溫暖。
他伸手想抱住璧君,卻又硬生生地止住了,手上緊握著拳,沒有將璧君抱在懷裡。蕭十一郎是發自內心、全心全意的愛著璧君,事事以她為先,處處替她著想,他自己從不為世俗所羈,也從不在乎別人如何看他,但璧君不行,名分上,璧君早已是連城璧的妻子,他決不能逾越了禮,而教璧君今後無法做人。
蕭十一郎道:「只要妳願意,我立刻帶妳走。」璧君卻立刻搖頭道:「不,連家堡…」此時,璧君真的好希望能與蕭十一郎遠走高飛,但卻立刻想到蕭十一郎,她擔心他們若真的一走了之,連家堡決不會放過蕭十一郎,而派人向他四海尋仇。奶奶錯了!是的,蕭十一郎能給他更多:蕭十一郎能給她信任;給她愛的溫暖;給他堅強的依靠,蕭十一郎總能在她最需要幫助的時侯出現,全心全意的幫助她、為她付出而不求回報,只要她能快樂的活著就好。而連城璧,總是一再的欺騙她、利用她、懷疑她,甚至在她最脆弱、需要受到保護和安慰的時候,替他擔心而阻止他去涉險的時候,居然誤會她、打她、責問她、羞辱她。面對如此夫君,沈璧君已然完全心死,再沒有任何情分,再不抱任何希望了。
她真希望能就此與蕭十一郎遠走高飛,浪跡天涯,但碰上的第一難題,便是這座屹立武林數百年而不搖的連家堡,蕭十一郎聞言,立即道:「我不在乎連家堡,我只要好過得好。」只要能讓璧君快樂,只要她能過得好,蕭十一郎願意付出他所有的一切,所有的一切。璧君又搖了搖頭道:「那我奶奶呢?沈家的名聲呢?」蕭十一郎道:「我知道,不能叫妳不在乎這些,是不是?那就留下。」璧君不住點頭。蕭十一郎知道,璧君身上永遠得擔負著沈家名聲的包袱,那是一個沉重卻不容她逃避的責任,一副永遠的枷鎖,就像他的護刀使命一樣。他不能要璧君不在乎這些,於是便勸璧君留下。蕭十一郎道:「我會陪著妳、守著妳,不再讓妳受半點委屈。」璧君既感動又悲傷地哭著。她知道,這輩子,再不用奢望連城璧能給他真愛;她也知道,這輩子,有一個人會永遠無怨無悔地愛著她、守著她,那是蕭十一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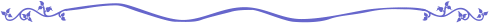
話說連城璧追擊逍遙侯,來到了連家堡後山,小公子被吊在山壁上,中了白楊、綠柳的「笑傲江湖」,仍在狂笑不已。逍遙侯欲救走小公子,被連城璧從半路殺出,兩人一番激戰,連城璧落於下風,但他先前埋伏下的白楊、綠柳等人及時搶出,用網捕住了逍遙侯,連城璧正想將逍遙侯的面具揭下,看清他的真面目,卻被逍遙侯使了一個爆炸逃脫,連小公子亦被救走,連城璧只好黯然而歸連家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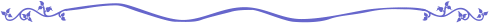
連家堡中,璧君房內,璧君經過了一晚的折騰,全身乏力地坐在床上,蕭十一郎哄她安心就寢。蕭十一郎道:「睡吧!」見璧君沒反應,知道她的心思,於是又道:「別怕!我會在妳門口守著,決不讓逍遙侯再有機會接近妳。」璧君仍餘悸猶存地道:「那你一直守著,決不離開?」蕭十一郎報以肯定而可靠的承諾,道:「我保證,妳醒來開門,第一個看到的會是我。安心睡吧!」璧君終於放心,點頭答應,準備就寢,蕭十一郎道:「我出去了。」璧君又微微點頭,蕭十一郎轉身走出房外。
蕭十一郎甫步出門,卻見連城璧已站在門口。連城璧語帶諷刺地道:「看來蕭兄是準備接下貼身護衛這一職囉?」蕭十一郎昂然堅定道:「是!」連城璧又以半諷刺的語氣道:「好,很好,有勞了。」說罷便要離開,蕭十一郎搶道:「你應該進去看看她的。」他既勸璧君留下,就仍希望他們能盡量好好地相處,希望連城璧能好好的待璧君,不要再讓她受到任何傷害了。可是連城璧哼了一聲,道:「有蕭兄守著,在下放心得很。」在蕭十一郎面前,他始終拉不下臉向璧君道歉認錯。蕭十一郎明白他心思,便道:「向妻子道個歉,應該不會有損你男人的尊嚴吧?」連城璧不理會,又諷刺道:「原來蕭兄還沒有忘記她是我連某的妻子。」他此言一出,本想將蕭十一郎逼得無話可說,自取其辱,不料蕭十一郎心中坦然無愧,慨昂道:「我記得比你清楚!」連城璧沒想到他竟會如此回答,說聲:「你…」便再也說不下去,蕭十一郎凜然道:「得妻若此,夫復何求?如果蕭某有幸得之,珍之惜之愛之信之猶恐不急,但少堡主卻一再拿夫妻情感來作試探,難道這就是待妻之道?」蕭十一郎一番肺腑之言,璧君聲聲入耳,內心既甜蜜又悲傷,甜的是,這世上,有一個男人如此深愛著她;悲的是,這個男人不是能與她廝守終身的丈夫。
連城璧也非常人,並沒有因為蕭十一郎的一番話感到羞愧難容、痛哭流涕,反倒又「哼」了一聲,道:「看來蕭兄是比在下更知道如何待她,如何討她歡心囉?」蕭十一郎不理會他的譏諷,仍平靜卻帶著尊嚴地道:「少堡主誤會了,蕭某只不過想提醒一句。」一句話還未說完,連城璧已然將他打斷道:「用不著!今天就算她死了,入的也是連家的祠堂,怎麼樣待她,是我連城璧的事,這輩子她過得好或不好,就看她自己的修為造化,還輪不到『蕭兄你』來操這分心。」這些話,有如銳針般,一根根扎入璧君心裡,蕭十一郎勸不動連城璧,只是沉痛得閉上雙眼,當他張開眼睛,連城璧卻已要離開,蕭十一郎仍叫著:「少堡主…」連城璧卻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蕭十一郎沉默了一會兒,對著房內的璧君,堅定地道:「我不會讓他對妳任性胡為,我絕不允許。」說罷,替璧君把房門關上。璧君在房內,獨自啜著泣,臉上,是悲傷難過的淚水,也是溫馨感動的淚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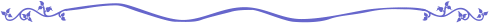
連城璧離開璧君的房間,走在綴滿燈籠的走廊上,揮手擊掉一個燈籠,燈籠掉在地上,燒了起來。他自言自語道:「連城璧,你是不是氣昏了頭了?你明明不是這麼想的…你明明是想向她道歉的…你怎麼回事?你…怎麼回事?」連城璧自己也不明白,他之所以會在璧君被折磨了一整晚之後,卻故意對她說出那種話,是基於對蕭十一郎的忌妒。因為他誤會了璧君,令璧君傷心、難過、絕望,蕭十一郎卻給璧君可靠堅定的承諾,給她關懷溫暖。他無法忍受自己在璧君心中的形象輸給蕭十一郎,他輸不起。
連城璧回到房中,要白楊、綠柳帶來了小公子,逼他畫出荒山地穴的地圖,小公子屈於他的威嚇,開始繪製地圖。連城璧心道:「璧君,等我抓住了逍遙侯,你就會明白,誰才是真正讓你依靠、教你心安的男人。」直到此時,連城璧仍以為,他可以用莫大的成功──為武林除去逍遙侯──來贏回璧君的心,全然不知,一份真正的情感,是要靠「愛」去灌溉的,而不是利益的交換。他是個可憐人,因為他不懂真愛;他是個可惡的人,他一次次深深地傷害著用真心愛著自己的人,一個可惡的可憐人,有另一個名字,叫做「可悲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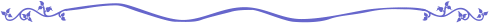
璧君早晨起來,走出房門口,卻不見蕭十一郎人影,心下黯然失落,想不到蕭十一郎如此可靠堅定的承諾,卻也沒能遵守。她正欲轉身回房,卻聽見蕭十一郎的聲音在背後響起:「我在這裡。」璧君回首,只見蕭十一郎站在大門外,心中寬慰,向蕭十一郎走了過去,又聽蕭十一郎道:「我在這裡,才能同時守著門和窗。」聽他如此一說,璧君心中更是備感欣慰,隨即,又有點心疼地問道:「你當真一晚沒閤眼?」蕭十一郎微微一笑道:「我不累啊!」璧君緩緩地道:「昨晚,我失態了。」目光幽幽地望著遠方。
蕭十一郎道:「少夫人,為什麼妳總要求自己做聖人呢?難道作了聖人,就能夠躲開凡人的喜怒哀樂嗎?」璧君搖頭道:「我沒有想過要做聖人,我只是希望,日子過得單純一點。」蕭十一郎道:「心理壓著痛苦,日子如何能單純?」蕭十一郎相當清楚,若璧君必須每天面對著從不給她信任、從不能以誠相待的連城璧,那份壓在內心的痛苦,是絕不能使她的日子過得單純快樂的。璧君道:「我…」卻不知該接什麼,蕭十一郎說的話很有道理。
蕭十一郎又微笑道:「其實在我眼裡,妳從來都沒有失態過。能看見真正的妳,我很開心呀!我喜歡!」語氣誠懇中帶著無限的包容與瞭解,也帶著無限深情。璧君悠悠地嘆道:「為什麼你能看到真正的我,而他不能?」蕭十一郎沒有回答。其實,他們兩人心中都明白,因為蕭十一郎能用真心待她,而連城璧不能。
正沉默間,忽聞城瑾慌張的聲音,只見她急匆匆地走來,對蕭十一郎道:「欸,欸!你還在這兒?!我大哥去找逍遙侯了你知不知道?」蕭十一郎疑惑地道:「昨晚沒有抓到他們嗎?」城瑾道:「昨晚讓他給跑了!走!我們快去幫我大哥。」說著拉起著蕭十一郎的手便要走。
蕭十一郎將她拉回,問道:「他怎麼突然就去啦?」城瑾道:「不突然,小公子畫了荒山地形圖了!」蕭十一郎一派輕鬆地道:「喔!既然有了地圖,加上妳大哥的聰明和身手,怕什麼?」城瑾天真地道:「也對。」她對自己大哥的本事可是深具信心的,但想了一會兒,又道:「可是…哎呀!不行啊!我還是不放心,走吧,走吧,走吧!」又拉著蕭十一郎要走,蕭十一郎依然靠著牆,站定不動,勸道:「欸!妳別忘啦,妳也中了毒,今天是第二天了!」一邊用手指敲著城瑾的頭,他這麼說,無非是希望城瑾別去涉險惹麻煩,城瑾卻仍天真地道:「那,抓到逍遙侯就不怕啦!」蕭十一郎問道:「萬一他寧死也不給解藥呢?」城瑾仍樂觀地道:「那…就找雪鷹。」蕭十一郎笑道:「呵,雪鷹早就逃走啦!」城瑾這下才慌了,跺腳道:「唉呀!壞了,我應該把他抓回來的,現在怎麼辦啊?」蕭十一郎道:「那妳聽我的啊,我先去幫你大哥,妳去找靈鷲想辦法,等妳好了,那我們要是還沒回來,妳再趕去。」城瑾聽了不住地點頭道:「好!那我先去找靈鷲了。」說完便走,找她的靈鷲去了。
蕭十一郎邊笑著,邊回頭看著璧君道:「不支開她,還不知她會闖什麼禍,我走了。」說著便要去幫連城璧。即使連城璧昨晚的行為如此不堪,但他還是璧君的丈夫,璧君和他終有夫妻之義,為了璧君,蕭十一郎會盡力保護連城璧的。而即使不為璧君,以蕭十一郎天生的俠義心腸,加上城瑾的請託,身為「連家下人」的他,也不會任連城璧去涉險送死的。
蕭十一郎正要走,卻被璧君叫住。璧君憂心地道:「十一郎…」蕭十一郎安慰道:「他不會出事的,我一定把他帶回來,好放心吧。」轉身正要走,璧君卻脫口而出道:「我不只擔心他。」蕭十一郎楞了一下,回頭望著璧君,但聞璧君續道:「我也擔心你。」蕭十一郎心中暖烘烘的,無論他受多大的傷,忍受多少委屈與誤解,只要有她這麼一句話,一切的付出都值得了。
璧君道:「我要一起去。」蕭十一郎立刻一口否決:「不行。」璧君道:「你我都知道小公子是什麼樣的人,他畫的圖,我們能相信嗎?萬一又是一個陷阱怎麼辦?」蕭十一郎還不等璧君講完,便道:「所以妳更不能去呀!」璧君堅持道:「我要去。」柔弱的聲音中帶著倔強的堅持。蕭十一郎又勸道:「璧君…」璧君道:「我一個人守在家裡更難捱,我想著你們可能會上當,可能會受傷…」說到一半,又被蕭十一郎打斷:「璧君!妳真的不能去。」語氣中也帶著誠懇的堅決。璧君道:「我要去!」蕭十一郎凝視著她,停了一會兒,情知拗不過,便道:「好,我帶妳去。要死,我們也死在一塊兒吧!」一句同生共死的承諾,蕭十一郎毅然決定,和沈璧君共赴逍遙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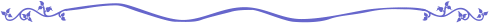
荒山,烈日高照,狂風呼呼地吹著,連城璧帶著大隊人馬連同小公子、白楊綠柳一齊前往逍遙窟,欲捉拿逍遙侯。大隊人馬先行,白楊、綠柳押著小公子跟著,連城璧殿後,忽地,草叢中一道黑影閃了一下,連城璧目光敏銳,早已察覺到,卻故意不動聲色,讓賈信帶著大隊人馬依原路而行,自己帶著白楊、綠柳連同小公子走另一條路,小公子邊走邊裝可憐,不住地呻吟道:「走不動了!」白楊、綠柳毫不放鬆,道:「走不動也得走!」
好個連城璧,賈信領著大隊人馬,才走沒幾步,逍遙侯埋伏的人便從四面八方躍出,頃刻間,雙方人馬已陷入一片廝殺,殺的天昏地暗,日月無光,連城璧卻早已押著小公子,協同白楊、綠柳,一同進入了逍遙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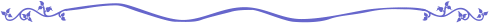
蕭十一郎與璧君攜手到了逍遙窟,眾人鬥得正酣,蕭十一郎對璧君道:「進去再說。」璧君點頭。但想要進入逍遙窟,必須先將那一大幫逍遙侯的手下打倒,蕭十一郎拉著璧君到一旁的大石邊蹲下,對璧君道:「我下去。」璧君仍點頭,眼神中充滿對蕭十一郎的信心與信任。
蕭十一郎凌空翻騰,飛躍而出,一眨眼,便已殺入人群中,數人圍將上來,只見他左拍右拿,翻身便是一個旋風,眾人皆莫耐他何,但璧君在一旁瞧著,卻也不免擔心,忽地,一個人被踢飛出去,摔在璧君旁邊,正巧觸動了機括,地上出現了一個大洞,璧君驚呼一聲:「蕭十一郎!」已然落了下去,蕭十一郎見璧君遇險,也無心戀戰,兩三下打發了圍攻上來的人,來到璧君落下的大洞邊,喊著:「璧君!」,跟著躍了下去。
蕭十一郎進入逍遙窟,走了幾步,發現前方出現了岔路,卻沒見著璧君,不禁有點憂心,才略一沉吟,他已自腰間拿出一樣物件,隨手在岩壁上刮刻了記號便向前走去,沿路上,凡他走過之處都在牆上留下了記號。
蕭十一郎方才離開,連城璧便已領著白楊、綠柳出現,看著蕭十一郎在岩壁上留下的記號,綠柳讚道:「哎呀!好聰明啊,這樣就不會繞相同的路了!」白楊也道:「對呀!」連城璧看了他們一眼,命令道:「你們兩個跟過去,找到逍遙侯之後,一個幫著蕭十一郎纏住他,一個馬上過來通報。」白楊、綠柳領命道:「好。知道了,走!」說罷跟蹤蕭十一郎而去。
連城璧遣了白楊、綠柳,獨自走向洞穴另一邊,璧君坐在那裡,被點了穴道,無法動作,也無法發出聲音,只用斜眼瞪著,小公子則被點了睡穴,睡倒在一旁。連城璧走過去,解了沈璧君的穴道,沈璧君第一句話便忿忿地道:「你利用十一郎!」此時,沈璧君對連城璧已不只是灰心絕望的冷感,憤怒鄙視更是兼而有之,連城璧仍大言不慚地道:「小公子的圖畫得太快,所以我不相信他畫的。」璧君簡直不敢相信,連城璧面對她的指責,非但不感羞愧,反而理所當然地做出這種回答,激動地道:「所以,你就讓蕭十一郎打前鋒去冒險?」連城璧反道:「那妳希望冒險的人是我,而不是他嗎?」想藉此堵住璧君的口。
璧君道:「我不要你們兩個人任何一個冒險,你不一定非要在這個時候打逍遙侯的,對不對?」連城璧道:「我們兩任何一個?這麼說,在妳的心裡,我和他的地位是一樣的了?」他沒想過,自己未盡做丈夫的責任,從沒給過妻子依靠和信任,卻要求璧君要給他不同於蕭十一郎的「丈夫的地位」。璧君忿道:「你…」頓了一下,才又道:「這個時候,你還有心思計較這些?」她真沒想到,連城璧身為武林至尊世家的「連家堡子孫」,在如此危險人命關天之際,在意的卻是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。連城璧道:「我告訴妳,我為什麼急著抓逍遙侯?因為我不要自己的妻子,為他而日夜擔驚受怕;我不希望自己的妻子,因此而認為我不能依靠;我也不要受他威脅,而不得不將自己的妻子,交給一位可能搶走她的人來照顧。若不解決逍遙侯的話,我只怕會…很快就會失去妳。」璧君道:「所以你不惜犧牲別人?」連城璧忙道:「他不是別人吶!他是蕭家的人,蕭家與割鹿刀有關,割鹿刀又和荒山地穴有關。」
璧君驚訝地道:「你在說什麼?」連城璧這才發現,自己在情急中,居然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心機,只道:「我…」卻語塞,接不下去,頓了一會兒,又故意道:「說了只會增加妳的困擾,不提也罷。」意欲粉飾太平,繼續蒙騙璧君,但璧君雖單純,卻並不迂,早已猜中了他的心思,道:「是你早已算計好了?你算準了蕭十一郎會跟來,所以你們就等在這裡,等他趕來自投羅網?」說罷轉身便走,要去找蕭十一郎。連城璧利用蕭十一郎的仁義心腸,利用他對璧君愛護照顧的心,利用他是蕭家人,料定他一定會來到逍遙窟,帶領連城璧找到逍遙侯。此時,璧君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,也看透了他的人格,不願再與他多說,只想儘快找到蕭十一郎,當她正要離去,連城璧卻一把抓住她的手,道:「璧君!」璧君厲聲道:「放開我,否則你現在就會失去我!」連城璧無奈,只得放開她,但見璧君離開,他卻又跟了上去,璧君回頭,不屑地道:「你可以不用跟來冒險,等在那裡啊!」轉身又走。連城璧仍不放棄,邊跟了上去邊道:「如果你出事了,就算我殺了逍遙侯又有什麼意義呢?」是的,如果璧君死了,即使他成功地殺掉逍遙侯,在這場競賽上,他仍是輸給了蕭十一郎,因為璧君,是為蕭十一郎而去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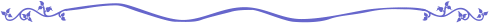
蕭十一郎一路奔至逍遙窟的大廳,洞內燈火通明,頂上還不時有水滴下,蕭十一郎正低頭沉思,不知璧君身在何處,忽覺身後有動靜,喝道:「兩個都給我出來!」只見白楊、綠柳兩老頭從岩後冒出,陪笑道:「嘿嘿!蕭大俠,是我們吶!」蕭十一郎一見是白楊、綠柳,立即恭敬地道:「兩位前輩,你們有沒有看到璧…」說到一半,發現在白楊、綠柳面前直呼璧君必竟不大合適,便改口道:「呃…我是說連夫人還有少堡主呀?」白楊道:「他們在一塊兒呢!」蕭十一郎又追問道:「平安無事?」綠柳答道:「安全得很呢!」蕭十一郎這才放心道:「那就好。」蕭十一郎雖是冰雪聰明,但是胸懷坦蕩,又一心只掛記著璧君,並沒有想到是連城璧設計自己去打前鋒,也沒有猜疑為何白楊、綠柳要跟蹤自己,但聽璧君平安無事,便心中寬慰。
蕭十一郎放了心,便又換回平日輕鬆頑皮的態度,雙手交叉在胸前,坦然無懼地道:「我們來看看逍遙侯,為我們準備了什麼樣的甕?」倒是白楊一聽,便立刻緊張得東張西望,不解地問道:「怎麼講?」蕭十一郎道:「這麼大的地方燈火通明,可走到現在,有沒有看到一個人影呢?」白楊、綠柳當真轉了個圈,把四周全看上了一遍,才道:「沒有。」蕭十一郎自信地微笑一下,道:「這不擺明了是請君入甕嗎?」白楊這可慌了,結結巴巴地道:「這、這、這、這麼多通道,從哪兒走啊?」蕭十一郎胸有成竹地道:「主人家既然好心指了明路…」還沒說完,白楊又急著問道:「什麼明路?」蕭十一郎續道:「當然是走點了燈的那條。」白楊還在遲疑,蕭十一郎已道:「走!」昂首闊步地向前走去,白楊、綠柳只得跟上去。
走到一處岩壁旁,綠柳忽地停下,對蕭十一郎道:「我說,這地方有點不對頭。」白楊也忙道:「我也感覺怪怪的,但是又說不上什麼。」蕭十一郎也發覺不對勁了,望了一下四周,指著岩壁道:「你們看!這是我剛才奔過時畫的線。」白楊驚訝地問道:「繞了半天,又走回老地方來啦?」蕭十一郎肯定地道:「不是老地方,在下沿牆一路畫過,可畫痕到這裡就斷了!」蕭十一郎正欲另尋出口,白揚卻忍不住碰了一下岩壁,忽然,岩壁發出一陣強光,產生了極大的吸力要將白楊吸進去,綠柳急忙出手相救,卻也和白揚一同被吸進了牆裡,蕭十一郎驚呼道:「前輩!」正欲出手相救,兩人卻早已不見蹤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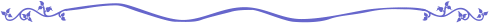
連城璧與沈璧君正走在逍遙窟的另一端,忽聞白揚、綠柳喊救命的聲音,璧君倒抽了一口氣,驚道:「那不是…」連城璧指向蕭十一郎所在的方向,道:「聲音是從那邊傳來的,是白楊、綠柳!」璧君點頭,連城璧又道:「咱們快過去看看!」璧君道:「好!」說著便往聲音傳來處走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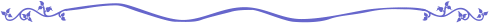
蕭十一郎站在岩壁旁,自言自語地道:「幻術!一定是幻術!」正思索間,又聽見後方聲響,他立時機警地道:「誰?」只見連城璧與沈璧君急急走來,連城璧問道:「白揚、綠柳呢?」蕭十一郎尚未回答,璧君已走到了岩壁旁,蕭十一郎趕忙伸手攔住,道:「欸!妳別過去啊!很危險的!」一雙明亮的大眼看著璧君,誠摯的關心之情溢於言表。連城璧在一旁看了不是滋味,輕咳了兩聲,蕭十一郎會意,便放開璧君的手,道:「吶!我讓你們瞧瞧,別怕。」這個「別怕」,卻是對璧君說的。
蕭十一郎從地上撿起一塊石子,丟向岩壁,壁上立刻閃起一道強光,將石頭吸了進去。連城璧驚道:「這麼說,白樣綠柳也…」蕭十一郎接道:「被吸進去了。」這時,連城璧關心璧君安危,將她往後拉,道:「小心,別再碰牆。咱們走吧!」拉著璧君便要離開,走到另一面岩壁前,蕭十一郎忽道:「等等!」也朝那面岩壁走了過去。蕭十一郎看著岩壁,搜尋著腦海中那遙遠的記憶,喃喃自語道:「上有天,下有地。左是爹,右是娘。中間有個小心肝。試試看!」言畢,伸手便朝石壁摸去,璧君一聲驚呼,抓住他的手,擔心地道:「別碰!」蕭十一郎看了看璧君,安慰道:「放心吧!沒事的。」璧君仍不放心,又道:「你可千萬小心!」蕭十一郎微笑道:「我會小心的。」
連城璧在一旁看著、聽著,卻早已氣煞,但也只好忍著不作聲。蕭十一郎看了岩壁一會兒,便伸手朝一個心型凹槽按了下去,頃刻,旁邊一道石門轟隆隆地打開了,璧君道:「門開了!」連城璧不想多面對蕭十一郎,率先從矮門鑽了過去。蕭十一郎微露喜色,自言自語道:「原來我沒忘!」璧君問:「你怎麼知道?」蕭十一郎道:「是我爹教我的。」蕭十一郎和璧君才逗留了這麼一會兒,石門那頭的連城璧已催道:「璧君!」蕭十一郎道:「進去吧!」忙推著璧君一同過了石門。
過了石門,蕭十一郎領先來到一處大石窟,仍不慌不忙地將手交叉在胸前,觀望著四周的環境。連城璧道:「這就是我們上次闖入的地方!」蕭十一郎看了看道:「那裡應該就是上回進去的大石窟了。逍遙侯應該在裡面。」連城璧道:「他可以藏身的地方很多,他要是不現身的話,我們是很難找到他的!不如,一把火燒了它。」此言一出,蕭十一郎立即道:「不能燒!」連城璧奇道:「為什麼?」蕭十一郎想了一會兒,道:「我不知道,但直覺告訴我不能燒。」連城璧心知蕭十一郎是蕭家人,和這荒山密穴、和割鹿刀都有莫大的關聯,他雖說不出原因,但卻直覺認為不能燒,那便真的不能燒,連城璧也只好作罷。
大家沉默了一會兒,蕭十一郎又好像想起了些什麼,緩緩唸道:「荷仙子,魚寶貝,青青水草兩頭隔,船兒船兒水中過。」須臾,一道石門又開了,連城璧仍率先進入,璧君隨後跟著,只有蕭十一郎還站在原地,沉思著那來自遙遠記憶的開門口訣。
忽地,隨著逍遙侯的一聲:「恭候多時!」一隻長臂已襲向連城璧,連城璧忙出劍抵禦。蕭十一郎見狀,也搶上前去,二人聯手,共抗逍遙侯,但連城璧終究功力相差懸殊,兩三招一過,他已撞倒在一座石台旁,手中長劍飛了出去。璧君一聲驚呼:「城璧!」衝將過去察看連城璧的傷勢,蕭十一郎一躍而起,接住連城璧的長劍,和逍遙侯鬥了起來。璧君見蕭十一郎獨戰逍遙侯,心急如焚,衝上前去,使出「沈家金針」,只聽「咻」、「咻」聲響,數根金針飛向逍遙侯門面,逍遙侯忙收回長臂,以袖子擋去了沈璧君發出的金針,趁這一瞬之隙,蕭十一郎已揮劍往逍遙侯的面部砍下,逍遙侯吃痛,化身而走。
但逍遙侯逃逸時,產生的勁力過大,蕭十一郎亦被摔了出去,一個觔斗,滾落在石台上,他身手敏捷,一翻身,便已下了石台,卻被莫名其來的力量牽制住,那只是一瞬間的莫名,接下來,他很快便意識到,石台是對他胸前的項鍊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。項鍊,掛在他的頸上,由於石台的強力吸引,蕭十一郎必須拚命用手支撐著身子,才不至於撞向石台。忽地,「咻」的一聲,項鍊斷了開來,往石台上的一個孔洞竄去,蕭十一郎趕忙出手抓住,這項鍊,是爹爹留給他的遺物,絕對不能掉。項鍊離石台越近,石台吸力越大,蕭十一郎右手握著劍,左手緊拉著項鍊不放,苦苦支撐,這時,石台開始震動,整個洞穴都在搖晃,忽地一陣響,石台分為兩半,蕭十一郎的手隨項鍊一同被吸了進去,一瞬間,石台便復合上,只聽蕭十一郎悶哼一聲,右手長劍掉在地上,左手已被石台緊緊夾住。璧君見狀,急呼道:「十一郎!」便要衝過去看他,被連城璧阻攔道:「危險!」璧君不管,掙開連城璧的手,衝了過去,問道:「十一郎,怎麼樣?」蕭十一郎拚命忍著痛,沒有回答。璧君對連城璧急道:「快想辦法!」連城璧和沈璧君便一人一邊,想要扳開石台,璧君既憐惜又心疼地對十一郎道:「挺住!」與連城璧拚命使勁,卻無法搬開時台。
此時,賈信帶著一幫人衝了進來,喊道:「少主!」連城璧道:「怎麼才進來了你們幾個?」他沒想到以連家堡能人之多、實力之雄厚,卻在殺進逍遙窟前便已折損了大半好手。賈信道:「是!」連城璧也顧不得還剩多少人能幫他消滅逍遙侯了,先讓人把蕭十一郎的手弄出來再說,畢竟面對神秘的逍遙窟與逍遙侯,日後還有用他「蕭家人」之處,並且,他也不想在璧君前再度因自己的器量狹小、利用他人而受到璧君的鄙視,他是連家人,連家人是從不求人的,也從不能讓人瞧不起。他到底還是有羞恥之心的,而且,他要保有他身為人夫的驕傲與虛榮,他絕不能被妻子瞧不起!因此,他忙道:「好!快進來幫忙。」
賈信帶著連家堡的人手,合同連城璧一起,正欲合力移開石台,卻聽見逍遙侯邪惡陰狠的笑聲傳來:「喝哈哈哈哈哈!蕭十一郎!幻室都困不住你,看來你當真是護刀後人了!」蕭十一郎痛苦地忍著,環顧四週,不知消遙侯的聲音是自何處傳出。賈信則張大了口,站在當地。連城璧催道:「那你幹麻!還不動手把台子劈開?」眾人一聽,都立即揮刀劈斬石台。
此時,又傳來消遙侯陰惻惻的笑聲,道:「哈哈哈!沒用的,除非以處子之血流入溝槽,否則它不會再開,不過等你們找來一個肯獻血的姑娘,他那隻手也早就廢了,喝哈哈!」
璧君聽他說到「處子之血」心中已是一動,待他說完,便再也忍不住,衝上前去要救蕭十一郎,卻被連城璧一把拉住,冷冷地道:「璧君!妳要幹什麼?」留著蕭十一郎雖然有用,但他決不允許璧君以血相救蕭十一郎,璧君是他的妻子,璧君的一切,只能屬於他。璧君堅定地道:「我要救他!」連城璧威脅道:「妳這一救,可知妳我之間會有什麼結果?」璧君看著蕭十一郎,只見他因疼痛而冒著冷汗,不斷地喘著氣,卻只咬牙強忍,一聲不吭,想起與蕭十一郎的過去種種,想到蕭十一郎對他的好,想到蕭十一郎幾次的捨命相救,想到蕭十一郎為了她而到消遙窟救連城璧,想到他們臨出發前對彼此的承諾──死也要死在一塊,於公於私,於情於理,她都有充分的理由和絕對的責任要救蕭十一郎。她又對連城璧說了一次:「我要救他!」連城璧豈不知這之間的輕重緩急、人情大義,卻仍阻止道:「璧君!」「我要救他!」璧君第三次堅定地說道。說罷,不再理會連城璧的反對,走到蕭十一郎身旁,對眾人道:「你們讓開!」
蕭十一郎立時阻止道:「妳別過來!」深怕她受到任何傷害。璧君承諾道:「我會救你。」蕭十一郎喘著氣道:「沒用的!他說的要處子之血。」璧君平靜地道:「我是。」蕭十一郎心中一震,瞪大眼,驚訝地看著璧君,又看看連城璧。他只道璧君早已與連城璧圓房,卻不知她如何還是處子之身。不僅蕭十一郎感到驚訝,在場所有的人也都覺得意外,賈信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望著連城璧,只見連城璧的臉上,亦憤亦恨亦尷尬。
璧君道:「還等什麼?把劍給我!」蕭十一郎這才從震驚中回過神來,一旦知道她仍是處子,知道她定要用血解救自己,便趕忙阻止,用剩下的一隻手猛把璧君推開道:「不要!」他不願璧君為救他而損了名節,更不願璧君受到一絲一毫的傷害,蕭十一郎即使手廢身殘,亦或性命不保,都不要璧君為自己血染石台,絕對不要!
蕭十一郎毅然道:「我不會讓妳這麼做的。」他急著要讓璧君斷了以血相救的念頭,心念一動,已有了計較,撿起地上的長劍,道:「我寧可自斷一臂!」話甫畢,一把劍已往自己的左臂斬去。他的劍揮得快,卻不料璧君的手擋得更快,一把接住了他斬下的劍。蕭十一郎既是決意自斷一臂,以成照護璧君之情、連沈夫妻之義,力道自然不輕,璧君用手掌接住,切下的傷口深切,鮮血,自她的掌心汩汩流出,滴入石台的凹槽,她卻仍緊握著劍不放。
蕭十一郎既驚訝又心疼地道:「妳…不要這麼做。」他情願犧牲自己所有的一切,也決不要璧君為自己受到傷害。璧君道:「難道你忘了,我的手,早已為你留下了印記?」是的,他們二人的手,都早已為對方留下了印記,那印記,是愛的承諾印記。蕭十一郎心中感動,還未說話,石台便已震動了起來,璧君一陣欣喜。
石台不斷震動著,一道強光從中間射出,剎那間,石台分為兩半,隨著璧君的一聲驚呼,二人已被震了出去,跌坐在地上,石台又復合併。
璧君一爬起來,忙握著蕭十一郎的左臂道:「你的手…」蕭十一郎卻也只顧璧君的傷勢,握起她的傷肢道:「妳的手…」璧君搖搖頭道:「沒事。」蕭十一郎確定了璧君的傷沒有大礙,這才注意到,自己與璧君的親密接觸、深情相許,早已使得站在一旁的連城璧氣煞。他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似的,怯怯的看了連城璧一眼,他並不替自己擔心,而是替璧君擔憂,她,畢竟是連城璧的妻子。
連城璧先是一臉憤怒,然後開始笑,狂笑,瘋狂地笑,絕望的笑,悲傷的笑,憤怒的笑,淒然的笑,慘然的笑。他邊笑著,邊緩步離開了逍遙窟,留下了不知所措的眾人。賈信尤其張大了嘴,傻在當地。
 回電視小說目錄
回電視小說目錄
|